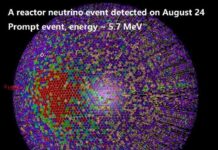中新社北京2月13日電 題:從東方到西方,“詩仙”李白何以情動世界?
——專訪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李春蓉
中新社記者 高凱
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的瑰寶與巔峰之作,李白的詩歌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舉足輕重,而且受到西方漢學界與文化界的廣泛關注與推崇。李白的詩歌以豪放灑脫、境界高遠、意境廣闊著稱,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深刻的思想內涵跨越了時空與文化的界限,穿越時空,不僅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持續探討與研究,亦深深打動西方讀者的心靈,激發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
李白詩歌何以突破文化壁壘,“詩仙”李白何以情動世界?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李春蓉近期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李白詩歌在西方的傳播狀況及其背後的動因等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李白詩歌在西方的傳播經歷了哪些主要階段?其主要特點和代表性事件是什麼?
李春蓉:1735年,法國耶穌會士杜赫德(Du Halde)在其編纂的四卷本巨著《中華帝國全志》中首次提到李白,“詩仙”在西方文化語境中的流播自此開啟。作為中國古典詩歌巔峰之作的李白詩歌一直受到西方漢學界、文學界的廣泛關注。李白詩歌在西方的譯介先後經歷了18世紀、19世紀的發軔期,20世紀上半葉的發展期,以及20世紀下半葉至今的繁盛期。
發軔期的代表性事件是歐洲“李白熱”的出現,這主要得益於傳教士的傳播、歐洲浪漫主義的興盛、詩人的創造性參與,以及歐洲對東方的神秘想象等;20世紀上半葉的發展期,中國學者的參與、中西學者的合作、西方漢學群體的學術交流促成了李白詩歌西傳的長足發展。這一時期,以李白詩歌為代表的中國古典詩歌對西方現代詩歌的影響上昇到新高度,甚至影響了現代西方詩學與詩歌創作。意象派詩人龐德(Ezra Pound)在美國掀起了以翻譯李白詩歌為代表的“唐詩熱”。1915年,龐德出版了漢詩英譯集《神州集》,全書共收譯詩19首,其中李白詩歌達12首之多。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基於中西文明互鑒的學界共識,以宇文所安、托洛普采夫、顧彬等為代表的漢學家共同建構了李白詩歌西傳的盛景,完成了李白詩歌西譯的“經典化”歷程。李白詩歌進入西方各國的權威性文學作品選集和工具書,進入大學課堂,成為經常被引用的經典篇章。
中新社記者:李白詩歌在西方社會的接受度如何?為何能吸引西方讀者?
李春蓉:自1735年至今,李白詩歌西傳已有近300年歷史。19世紀歐洲的“李白熱”、20世紀美國的“唐詩熱”都充分表明李白詩歌在西方存在廣泛傳播。西方國家研究者通常把李白與本國的偉大詩人相提並論,這也體現了李白及其詩歌被接受和欣賞。在西方讀者眼中,李白是比肩古希臘詩人阿那克里翁、德國詩人席勒、英國詩人華茲華斯、俄羅斯詩人普希金的偉大詩人。
至於李白詩歌為何能如此吸引西方讀者,我認為首先是詩人特立獨行的性格特點,其次是詩歌創作天賦。正如英國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所言,李白以“自負的文字功底”和“天才的直覺”使其詩歌飛揚飄逸,並激發讀者心靈深處的共鳴。李白詩歌之所以吸引讀者,不僅在於其非凡的語言表達能力,更得力于其詩歌所具備的情感張力。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也認為,李白的詩風獨特,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是形成詩人獨特風格的根本原因。其跌宕酣暢的詩歌語言,來自于天才的靈感,因而無可比擬、無從效仿。
中新社記者:李白的詩歌有大寫意的東方審美趣味,從您的研究出發,您認為李白詩歌的哪些特質使其能够跨越文化和語言的障礙情動世界?
李春蓉:我認為,在西方漢學界,李白是唐詩乃至中國文學史上一個不可替代的表徵。李白詩歌中“欲上青天攬明月”的浪漫情懷、“扶搖直上九萬里”的自由灑脫、“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樂觀精神等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認同,超越時間與空間,不斷激起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間的碰撞與共鳴。這些特質使其能够跨越文化和語言的障礙,穿越時空,情動世界,在西方文化語境中受到廣泛關注。
法國散文家、文學評論家蒙太古從比較文學的視野,審視來自神秘東方的李白與德國浪漫主義詩人海涅的詩作。蒙太古敏銳捕捉到了李白與海涅的相通之處,並從中西方異質文學中找到了相似的文學內核——抒情性。蒙太古認為,抒情詩這種頗具創造力的文學形式有力地證明了中國人與歐洲人,在豐沛情感的表達上所擁有的共通之處。
中新社記者:詩歌走向世界,為西方讀者所熟知必然要通過翻譯,李白詩歌的翻譯面臨哪些主要挑戰?應如何克服這些挑戰?
李春蓉:比較文學學者曹順慶先生曾說,翻譯作為一種語言形式的轉換過程,變異在其中如影隨形。
翻譯是李白詩歌走向世界的關鍵。如何將李白詩歌的文化意象、詩歌意境、感情色彩和想象因素納入他國的文化土壤並獲得“後起的生命”,是譯者面臨的重要問題。
以唐詩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海外傳播,必然需要通過翻譯實踐去開啟傳播與接受的途徑。然而由於中西文化差異,經過譯者的文化過濾,不可避免地會生發出種種剝離於原義的誤讀和變異。如何盡量減少誤讀和變異,是中國古典詩歌翻譯研究必須面對的挑戰。
我認為,中外合作是更好的模式——中國譯者把握內容不被曲解,同時給予母語譯者在叙事和表達方式上的充分自由。基於中西語言文化的差異,面對不同受眾,應採取不同的翻譯策略。
針對西方普通大眾讀者對中國文化尚存較大“認知差”的現狀,我們應給予“認知差”彌合過程足够的時間和耐心,對於優秀譯者的專業判斷,也要給予更多尊重與信任。某些情況下,譯作中存在適度的變異,有利於消除普通讀者的閱讀障礙,降低認知難度,增加譯文的可讀性,擴大傳播的受眾面。
對於學術研究性譯本,譯文應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這有利於推進中西學術交流。例如,在翻譯唐詩裡的中國古代樂器“瑟”時,詩人約翰·特納的英文譯文“zither”採用了音譯的翻譯策略,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傳播中國文化,促進學術交流;詩人威特·賓納則在譯文中使用西方樂器“harp”(竪琴)來翻譯“瑟”,目的在於增加譯文的可讀性和傳播面。
中新社記者:作為一位研究者,您認為李白詩歌在西方的傳播歷程及其影響對於東西方文化交流有何價值啟示?
李春蓉:詩人歌德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作為世界文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唐詩是中國精神的文化表徵。唐詩之所以能“走出去”並在異域土壤落地生根,緣於其體現的東方詩歌美學與西方詩歌美學的深度契合。
詩歌是全人類表達精神世界的共同藝術形式。李白詩歌在西方的譯介既是中國文學外傳的代表,也是中國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典範。自1735年至今,李白及其詩歌的生命力在西方文化視域中得到了擴展和延伸,藝術魅力長盛不衰。中國詩歌在西方的譯介與傳播既是中國古典文學生命力的延展,也是人類文化交流的美麗之約。今天的中國致力于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進一步通過以詩歌為載體的文學叙事來傳播中國聲音,將會為促進中西文明對話與交流添加濃墨重彩的一筆。(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