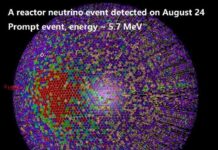中新社上海5月11日電 題:行萬里路:奧雷·伯曼騎行手記對和平的感悟
作者 李姝徵 周孫榆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句中國古諺,卻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荷蘭學者奧雷·伯曼(Ole Bouman)的經歷。
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作家、城市設計和建築策展人,2024年2月,同濟大學外籍教授奧雷·伯曼騎上自行車,從阿姆斯特丹出發,途經維也納、伊斯坦布爾、德黑蘭、烏魯木齊、洛陽等多個城市,歷經156天,橫跨10756公里。同年7月,他最終抵達上海。
為了理解“東方”的蘊意,奧雷·伯曼沿著絲綢之路,踏上屬於自己的“東遊記”。而後,他強烈地意識到:需要基於這段經歷寫下一本書,來分享這份理解,“特別是在這個誤解加深、分歧加劇的時代。”
近日,奧雷·伯曼的騎行手記即將完稿。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奧雷·伯曼說:“我希望這本書為有意維護世界和平的人帶去啟發”。
萬里路後一卷書
當奧雷·伯曼在電腦上敲下書稿的第一個字時,他發現自己正“重蹈覆轍”——每天在空白文檔裡掙扎,比騎行萬里更煎熬。寫作的孤獨遠超騎行,祗有光標在屏幕上無休止地閃爍。“我並非天生擅長寫作,這簡直是場戰鬥。”奧雷·伯曼坦言。
在孤獨、挫敗和焦慮中,奧雷·伯曼堅持在寫作之路上緩行,一如他一路向東的旅途。
當世界已習慣科技賦予的“加速度”,奧雷·伯曼為何仍堅持以車輪和文字,去丈量文明的褶皺?
“和平需要對話,而真正的對話需要掙脫時代的‘加速度’。”人類要真正地理解他者文明,需要以血肉之軀的溫度去融化偏見的冰層。“而這注定不會太快。”奧雷·伯曼說。
“人類需要攜手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更是能瞬間毀滅文明,”在奧雷·伯曼看來,當今的世界比以往更需要合作而非對抗,為理解他者所作出的每一分努力,都彌足珍貴。
“我不是‘中國迷’”
在寫作中,奧雷·伯曼也試圖探討自己與中國的“羈絆”。
2005年,他初次飛往中國,其後數年間,奧雷·伯曼舉辦了他在中國的第一次講座、第一場展覽。2015年,奧雷·伯曼選擇長期留在中國。十年來,他先後擔任第五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創意總監,改造老玻璃廠房,建立新博物館,又受邀成為同濟大學的外籍教授。“某種難以名狀的引力始終存在。”奧雷·伯曼說。
“我不願被簡單歸類為‘中國迷’,這個詞太輕飄了。中國並不是一個足球俱樂部。”與中國長達十年的“對話”讓奧雷·伯曼意識到:真正的文化探索需要經歷睏頓,而挫折恰恰構成了認知的厚度。
在數字技術空前發達的當下,對他者文化的接觸越便利,越容易陷入淺嘗輒止的幻覺。在奧雷·伯曼看來,真正的文化自覺,不在於固守或拋棄,而在於保持對惰性的清醒認知,並持續不斷地克服懶惰。
少有人走的路,卻有獨特的風景。
2024年3月,在抵達伊斯坦布爾前幾小時,奧雷·伯曼在馬爾馬拉海邊見到一尊巨型雕像——那是土耳其作家亞沙爾·凱末爾(Yashar Kemal)。
亞沙爾·凱末爾窮盡一生心血在文學疆域構築橋樑——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思想鋼索,串聯安納托利亞高原與歐洲大陸的文明棧道,縫合土耳其與庫爾德民族間的歷史裂隙。
在凜冽的寒風中,奧雷·伯曼望向亞沙爾·凱末爾的雕像。“他因倡導對話而飽受誤解,正如我騎行六個月欲促進與東方的對話,卻發現許多人寧願秉持爭議性議程,因為‘理解’無益於利益爭奪。”奧雷·伯曼說。
對話歷史與當下
沿著絲綢之路騎行,在奧雷·伯曼看來,他旅途中的每一天,都在與不同文化、不同地區的歷史與當下對話。
書寫過程中,途中許多場景隨著奧雷·伯曼背景知識的豐富而被發掘出更多含義,這場漫長的對話也更顯韵味悠長。
回溯遊覽嘉峪關的經歷,奧雷·伯曼感覺有些過於“熱鬧”了:城牆上擠擠挨挨的遊客、兜售各色旅遊紀念品的攤位,甚至還有身著明代鎧甲的“關長”……奧雷·伯曼轉身遠望另一側——遠處戈壁殘存的沙丘中,矗立著一座工廠。
他遠眺向廠房煙囪時,虛構的歷史圖景突然與當代中國產生了連接:正是這些日夜運轉的工廠,才支撐起打造這片“古代文化景觀”的可能。“要建博物館,先得建工廠——這何嘗不是中國發展邏輯的縮影?先完成現代化的‘奇跡’,才能培育出擁有度假需求的中國消費群體。”奧雷·伯曼說。
在西寧,奧雷·伯曼跟著一個提著兩個鳥籠的老人走了10分鐘。“等紅綠燈時,他小心翼翼查看鳥兒的模樣,那種對愛寵的珍視與自豪,瞬間讓市井街角變成了屬於他的完整‘小世界’。”這一幕在奧雷·伯曼眼中,超越了文化差異,也超越了時空,“當我們學會為一個陌生人的鳥籠停留,和平就有了最小的計量單位”。
當遊客散盡,奧雷·伯曼品味了在敦煌的獨處時刻。“我夜行莫高窟,唯聞風聲鳥鳴與千年佛窟相對。”奧雷·伯曼說,在那一刻,他既能感知歷代僧侶修行時的寧靜,又能洞見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共性——無論是留下壁畫的畫師,提著鳥籠的老人,還是戈壁灘工廠裡的工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編織生命的意義。
西出陽關有知己
決意遠行,也許需要一些“莫愁前路無知己”的達觀。
旅途中“知己式”的共鳴,不僅是奧雷·伯曼與不同文化背景人們的善意互動,更是一種穿越時空,與古代旅人的“心意相通”。
在敦煌,奧雷·伯曼深入戈壁,去見證漢朝邊疆的遺跡——逶迤的長城與三座雄關交匯——酒泉、玉門關、陽關,歷經近兩千年風霜,依舊巍然。
“站在陽關前,我立刻想起了王維的《送元二使安西》。”奧雷·伯曼輕輕吟誦,“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詩句驚人的寫實。“那是一種壓倒性的孤寂,黃褐色無垠的蒼涼,風在斷壁殘垣間呼嘯的銳響。”奧雷·伯曼說,時空仿佛在此凝固,兩千年未改顔色。
沿著曾經的邊境線西望,奧雷·伯曼突然深切體會到絲路旅人踏入未知時的心境:一旦西出關隘,便墜入無垠荒蕪。
“但更深的頓悟隨即擊中我:原來我的旅程同樣壯闊。”從阿姆斯特丹出發,奧雷·伯曼一路向東,穿越無數邊界:有形的、無形的;歷史的、文化的。他多少次抵達目力所及的遠方,眼前再度昇起新的地平線——每次抵達都意味著更遼闊的啟程。
唐代玄奘西行求法入陽關曬經,漢代張騫兩次出使西域,更有數千年間無數往來遠行於絲綢之路上的旅人……在陽關前,奧雷·伯曼幻想著這一串串腳印、一幕幕歷史,“若他們有知,或許亦會生出‘西出陽關有知己’的感慨”。
“我甚至幻想著與那些準備啟程的古代旅人對話,告訴他們:陽關之外雖有胡沙與塞塵,也有無數善意的面孔。”奧雷·伯曼說。(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