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的花園》的出現,無疑為當代文學增添了一種融國際視野、歷史深度與懸疑審美於一體的獨特創作實踐。它不僅延續了作家吳民民一貫的悲劇色彩與歷史意識,也再次佐證了以“逃”與“追”為書寫核心的敘事策略,如何引領讀者在跨越國界的亂局中,對正義與邪惡、愛與死、生與滅等命題發出新一輪拷問。其恢宏的格局與深沉的情感,使之成為一曲在“冬季”奏起、久久回蕩的文學悲歌,值得讀者與評論界長期回味與評鑒。』
在愛恨交織中走向終極悲涼
——評吳民民長篇小說《冬季的花園》
文 | 任 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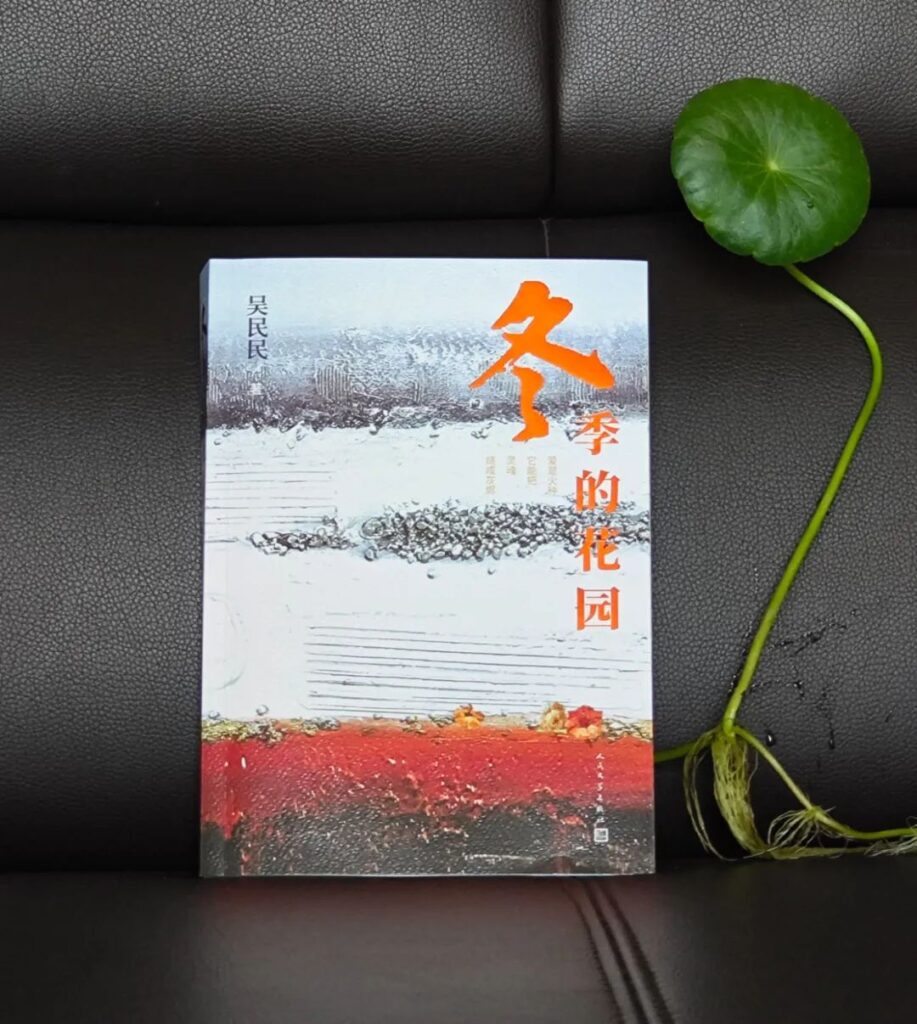
在當代中國文學的廣袤版圖中,有一位特殊的作家,他的筆觸跨越了區域與民族的邊界,在國際政治與戰爭的宏大背景下,將一個個血肉豐滿、命運多舛的個體形象鐫刻在歷史與時代的坐標系裏。這位作家便是吳民民。其最新長篇小說《冬季的花園》(人民文學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正是他對中國近代史與日俄戰爭題材的一次新探,揭示出波譎雲詭的亂世之下,人性與欲望、情感與宿命、國家與個人糾葛碰撞出的生命火焰,也映照著作家本人對歷史、對社會、對人性持久不變的深切關懷。
在這部長達三十九萬字的浩大作品中,吳民民將“逃”的元素深植於人物命運和故事結構之中:嚴一龍、高虎娃、許文娟,乃至警探安勇,皆徘徊於悲喜的深淵,體會“追”與“逃”交錯的痛苦。倘若說“逃”是一種手法、一條線索,那麼它所串聯起的絕不僅僅是個人的生死去留,更是對那個亂世浮沉的深刻反思,以及對愛情、信仰、悲劇與救贖的多重叩問。本文將圍繞該小說的寫作手法、結構方式、文字表現、歷史背景、風格繼承與美學意義等多個維度展開論述,力求以宏觀透視和微觀剖析結合的方式,探尋《冬季的花園》在當代文學中的位置與價值。
多重時空與群像刻畫的交織
繁複卻清晰的多線佈局
《冬季的花園》的故事脈絡可以用一句話概括:以嚴一龍、許文娟、高虎娃為核心的亂世三角關係,輻射出中日俄三方乃至地方軍閥、革命黨、流氓幫派等多股力量的彼此盤根錯節。作家在策劃這一繁複結構時,明顯借鑒了大場景、大格局的寫法:人物眾多卻井然有序,歷史轉折的節點與人物命運的關鍵時刻彼此融合,形成層層推進的雙向動力。
在文本的分章與段落中,作者採用了大量鏡頭式跳轉和對照:比如旅順前線的慘烈與日本弘文學院的平靜課堂交錯出現;既有遠景式的群體廝殺,也有特寫式的個人淒苦內心;既寫日本黑幫“白虎會”如何插手中國革命,也寫北洋新軍或奉系軍閥如何將百姓裹挾到死局之中。多種場景的穿插有助於為作品鋪展氣勢,也最大程度地拓寬了作品的時空範圍。
這種繁複結構的優點在於,可以真正塑造群像——讀者不僅能看到嚴一龍與許文娟的感情悲歡,也能在員警安勇的視角下窺見那個年代員警、地方官僚與黑白兩道的微妙關係,還能在高虎娃、李玉強等人身上體會不同階層、不同性格的人物在亂世之中所面臨的生死選擇。人物雖多,但被多個主題與事件巧妙地串聯,整體顯得清晰而富有層次感。
主線與暗線的交織:戰爭與愛情的雙重悲歌
在這樣的大結構之中,既存在一條顯而易見的主線,即嚴一龍橫跨中國與日本、在多個政治勢力之間左右奔走的冒險旅程,也存在若干暗線:它們或是愛情的暗流,或是政治陰謀的策動,或是黑幫利益的算計,甚至也有革命黨與諜報機關錯綜複雜的地下活動。主線與暗線互相交叉、互為增補,使得小說不僅僅是一部生動的戰爭史詩,也是一部對人性多重矛盾與扭曲的深邃描寫。
最顯著的一條暗線來自女性視角:許文娟和高橋百合子,一個生於偏僻農村,卻被推上命運洪流的中國女性;一個是日本黑幫大佬之女,在激情與國族立場之間搖擺的異國女子。兩條女性線索一明一暗地在嚴一龍的人生軌跡中交錯出現,既是溫柔慰藉,也帶來危機與毀滅。在大多數描寫戰爭與歷史題材的小說中,女性往往成為附屬或陪襯。而在《冬季的花園》中,許文娟的命運與百合子的情感糾結卻時時左右故事走向,更令全書迸發出淩厲的悲劇氛圍——她們或以愛為生,或以恨為念,卻都無法超越時代的厚壁,終究只能逃往一處荒寂或凋零之地。
以“逃”貫穿全篇的敘事策略
“逃”的多重功能:故事推力與隱喻象徵
在《冬季的花園》中,“逃”這一動作貫穿全篇,既是故事最直觀的推動力,也隱喻了人物內心對殘酷現實的抗爭與對理想之地的追尋。嚴一龍逃離日俄戰爭戰場、逃向日本治傷求學、再逃回東北,又因捲入凶案或軍閥勢力角逐不斷奔逃;許文娟則在平凡女子的“盼嫁”與亂世紛擾之間四處漂泊,終至落入更深的絕望;高虎娃、警長安勇以及其他人物,也都被革命與反革命、愛情與背叛、利益與陰謀推動,不得不在九死一生的邊緣不斷上演“追”與“逃”的戲碼。
“逃”的動作在故事層面首先是情節發展的抓手:幾個核心人物之所以能夠交織在一起,正緣於“逃亡”與“追捕”形成的張力。隨著人物“逃”離一個漩渦,又捲入新的漩渦,讀者持續被帶入下一個高潮,敘事節奏得以保持緊張、懸疑。而在隱喻或象徵層面,吳民民賦予“逃”以更深廣的內涵:歷史大勢如滾滾洪流,身處其中的個人無論是出身富貴還是貧賤,都沒有真正擺脫命運之網的可能。就如同《悲慘世界》中員警沙威與冉·阿讓之間的“追”與“逃”。而一旦撕去表面的善惡判斷,雙方其實皆為時代的囚徒——他們在各自的軌道上無盡賓士,卻難以擺脫宿命的陰影。《冬季的花園》中,嚴一龍與安勇、許文娟與百合子、高虎娃與李玉強等人之間的糾纏,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在這一系列“逃”與“追”的交互中,作者持續向讀者拋出問題:這些人究竟想從哪里逃?逃向哪里?他們的最終歇腳之地又能否給他們以片刻安寧?隨著故事走向尾聲,我們發現所謂終極的逃離並不存在。正如小說的標題,“冬季的花園”象徵一種白雪皚皚下的冷寂隱逸,實則隱喻那些被時代洪流裹挾過後、身心破碎的靈魂只能在冰冷的冬季找到暫時的停駐。這種由“逃”而不得的深重悲劇感,構成了小說獨特的基調。
歷史派懸疑筆法:以“大仲馬式”掛史編事
作為一部宏大的歷史小說,《冬季的花園》在寫作手法上具備明顯的“歷史派懸疑”特徵。作家並未將懸疑偵探或驚險情節當作單純的噱頭,而是借其強化歷史悲劇背景下人性裂變的質感。偵破與推理由外部形式轉化為人物內心的暗流湧動:嚴一龍、許文娟、高虎娃、百合子等多條感情線索和命運糾葛隱藏著懸疑的伏線,而警長安勇的偵緝則像一條明暗交錯的主線,一次又一次迫使主要人物暴露內心秘密。
評論家潘城指出,這種做法與法國作家大仲馬的歷史小說頗有相似處:在大仲馬那裏,歷史事件像一只只釘子,把虛構情節或虛擬角色“釘”在史實之上,讓人物與真實歷史平行存在。吳民民則在歷史脈絡的基礎上,同樣採用了類似的“掛史”創作策略:日俄戰爭、武昌起義、天津起義、辛亥革命、鄭家屯事件、北伐戰爭,乃至九一八事變的腥風血雨,都成為小說的時空支柱,伴隨著主要角色在不同地區與勢力之間的穿梭。而在“掛史”之外,懸疑、推理、逃亡等文學元素就像一張網,把人物的情與恨、理想與失落都包裹進來,讓整部小說既具有歷史的厚重感,也保持了閱讀時的一波三折與引人入勝。
直抵人性深處的悲憫與殘酷
紀實與虛構、簡練與張力的融合
吳民民早年的文學起步與紀實寫作密不可分,《中國留日學生心態錄》等報告文學作品曾先後獲獎,其扎實的採訪功底與豐厚的史料積累,為長篇小說的敘事奠定了踏實的基礎。創作《冬季的花園》時,他既深入研究了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之間的多國歷史,也將自己遍訪歐洲與日本檔案館收集到的第一手文獻融入細節之中,令作品在歷史真實層面達到了高度可信。
然而,這種真實性並未妨礙作家在語言和情節處理上的精巧虛構。他一方面十分注重場景的寫實質感,務求在每一次戰爭、暗殺、逃亡或審問的描寫上栩栩如生;另一方面,又能夠在對話與細節中加入高度個性化的虛構因素,使角色的形象更具文學魅力。例如,高虎娃這個名字本身便頗具象徵意味:出身貧苦的長工,自幼便蘊含“虎”之野性,又註定將在情感與理想的泥沼中掙扎。作家通過幹練卻頗具張力的語言,折射出人物複雜矛盾的內心。
詩意化瞬間與白描式悲涼
在敘事之餘,吳民民也常常以散文化、詩化的瞬間,為戰爭的慘烈與人物的苦難賦予另一層審美意味。譬如在描寫嚴一龍與許文娟初次重逢,內心劇烈震盪之際,作者筆下卻給讀者展示了夜幕低垂、大連海港閃爍的燈火、遠處海浪聲混雜著人群喧嘩的景像。一切寂靜的夜色如同無聲的見證者,配合人物隱忍而深切的內心獨白,使讀者直觀感受到歷史大潮沖刷下個人命運的孤獨。在對風雪中思無量庵的景象刻畫時,那種大雪覆蓋、冷寂孤絕的意象與人物悲苦宿命產生強烈對照,這種白描又有詩意氛圍,讓冰與雪映射蒼茫世態。
這樣的文字風格讓人想起日本戰後社會派小說大師水上勉或松本清張在刻畫社會陰影、個人罪孽時偶爾閃爍的“靜美”之筆,但吳民民更執著於對中國東北地區廣漠蒼莽的自然環境轉換為一種象徵性符號:“冬季的花園”既是埋葬者的悲涼,是不可回溯的命運象徵,也是歷史悲歌最後的迴響。
清末民初的政治與國際關係視野
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遠東時局的轉折期
《冬季的花園》之所以在當代文壇頗具獨特價值,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它的時間與背景選擇。國內歷史小說對抗日戰爭或晚清變法、戊戌政變等題材關注較多,但很少有作品將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這段相對冷僻卻決定遠東政治格局的時期作為主軸。這也顯露出作者在國際政治史領域的深度介入與眼界。
1903年左右,滿洲地區“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使日本軍隊得以堂而皇之地進入東北,並與俄羅斯帝國展開殘酷的爭奪。清政府雖打著“中立”幌子,實則既希望倚靠日本人趕走俄國勢力,又懼怕日本最終染指中國東北。但隨著日本戰後在滿洲利益的不斷擴大,俄國勢力雖被部分擠出,中國百姓反成最大的犧牲品。此後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中國進一步陷入軍閥割據、外敵環伺的絕望境地。再然後,直到1928年北伐完成和1931年九一八事變,又是一場巨大的風雲變幻。
吳民民精准地捕捉到了這段變局時期:它非但未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復興,反而演變成新的屈辱和軍閥混戰,而日本則在東方世界崛起為真正的霸權力量。這種歷史真實,透過小說中地方軍閥、日方黑幫、革命黨人等多方勢力的紛爭博弈,呈現為一幅血與火的畫卷。正因此,小說不僅僅是個人的命運劇本,更是世界大動盪年代的遠東秘史,為讀者理解近代中國與東北亞局勢演化提供了頗具深度的文學視角。
小人物的苦難:跨國視野中的悲憫
在《冬季的花園》中,最動人之處並非那些政治大人物或軍閥,而是嚴一龍、高虎娃、許文娟等在歷史風雲下掙扎的“小人物”。他們的苦難擁有最厚重的說服力:從旅順黃花崗村的抓鬮派民夫,到李玉強父子在俄勢力餘威下遭遇財產沒收與族群仇恨,再到大連紫金閣裏中日混雜的下層人等,這些渺小的面孔所承受的屠戮與淩辱,才最能體現那一時期人民飽受踐踏的真實境況。
與此同時,作家又設置了高橋家族這樣的日本角色,通過白虎會掌舵人高橋旭與兒子高橋正夫、女兒百合子等人物,說明了日本國內政治勢力和黑幫勢力的各懷鬼胎。對於日本所發動的侵略,作家採用更為複雜的表現:既揭示其侵略本質,也塑造出像百合子這樣富有同情心、願意幫助嚴一龍甚至支持中國革命黨人的美好形象,以此昭示“日本人”這一整體身份下多元的面孔。跨國視野讓小說遠離臉譜化,有了悲憫、深邃的歷史觀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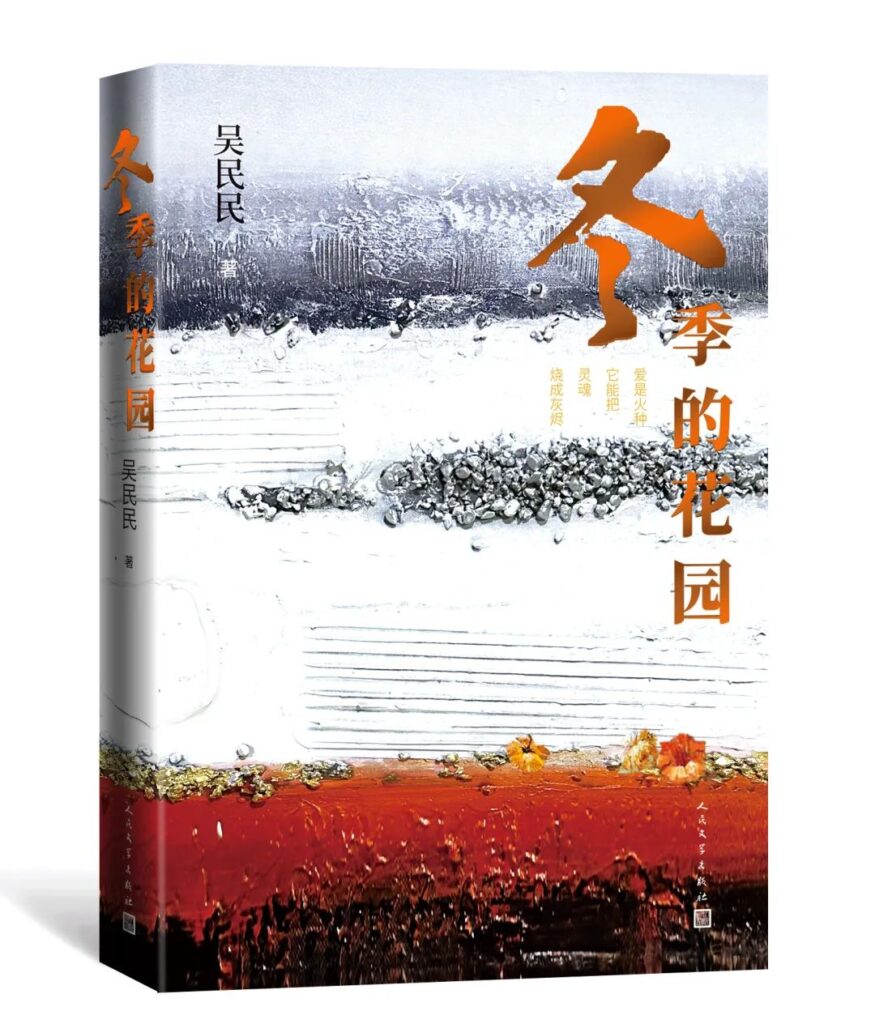
從社會派走向歷史派的開拓
社會派懸疑的承繼與超越
吳民民長期旅居日本,曾與戰後日本社會派推理大師水上勉、松本清張等有私交。他在其前作《海狼》《世紀末的挽鐘》等長篇小說中,就已顯現出以複雜社會矛盾為背景的懸疑策略,將偵破、推理與戰爭、權力、政治、經濟等要素有機結合,被評論者稱為社會派懸疑的典型。然而,《冬季的花園》又進一步擴大了視野,將時空跨越到清末民初那場漫長的中日關係史,不再著力探討現代社會陰暗面,而是將歷史、政治、國際關係與懸疑手法相結合,創造了更具史詩感與悲劇力量的文本。
某種程度上,水上勉、松本清張所開創的社會派,在《冬季的花園》這書本裏被推向了歷史派:懸疑成為燭照歷史黑暗與人性悲劇的探照燈,而非文本自我封閉的技藝展示。讀者在享受緊張刺激的情節節奏時,不得不直面橫亙在文本之上沉重的歷史鐵板。這樣的轉化,標誌著作家對懸疑、推理的功能定位更加多面化,也展現出他繼續探索大型歷史題材的強烈雄心。
與自身創作脈絡的呼應:傷痛與悲劇之美
就吳民民個人創作史而言,《冬季的花園》也繼承了他對悲劇格調與尖銳人性剖析的一貫追求。從早期紀實文學的社會調查,到後來專注反映二戰期間太平洋戰場、遠東戰場的大型歷史小說,吳民民對戰爭這一極端環境下人性的複雜始終保持著深入興趣。無論是先前的《世紀末的挽鐘》《海狼》還是如今的《冬季的花園》,人性的殘酷、傷痛與隱忍無處不在,悲劇意識與心靈救贖形成了貫穿他的創作生涯的主題。
具體到《冬季的花園》,故事最終在思無量庵的雪地與滿目凋零的花園中收束:愛與恨都歸於靜默,曾經如火如荼的掙扎都化為墓地或寺廟的餘灰——“冬季的花園”恰似作家對悲劇之美的一次深沉凝視:冬季本是蕭瑟與死亡的象徵,然而,也正是在淩寒中或許才蘊藏某種極致的純淨。小說的結尾呈現出無言的靜默與宗教意味,將宿命、罪孽乃至生死都歸結在無路可逃、無人可解的空茫之中。此種悲劇美學與作者的過往寫作脈絡遙相呼應,使得《冬季的花園》既是一部歷史題材的新拓,也是作者在創作主題和風格傳承上的延伸與昇華。
宿命、悲憫與對無處可逃的終極叩問
悲劇意識的強化:人性的囚籠與破碎
整個閱讀過程中,讀者最難忘懷的即是悲劇氛圍:從戰爭開篇到亂世落幕,無論嚴一龍、高虎娃,還是許文娟、百合子,都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安寧。他們的每一次努力、每一個抉擇,似乎都在加速走向新的深淵:背叛、誤殺、蒙冤、苦戀無果、殘酷的權力鬥爭……一重疊一重的困境提示我們,這是一場無可逃遁的宿命之局。
吳民民的悲劇意識注重燭照人性幽暗的角落。不是所有人都註定墮落,卻在亂世中“不得不”扭曲,暴烈被放大。譬如高橋正夫與高橋旭父子的黑幫身份,不僅是“壞人”,也有內在的血親羈絆與民族立場;許文娟終被迫“逃”入空門,不是因為她有出塵的信仰,而是愛恨交織下的心力交瘁,唯有靠與世隔絕的方法實現掙脫。悲劇在這裏彰顯出每個角色內心的微光:在苦難中的一點點溫暖與善意,更令人唏噓感慨。
對亂世情感與個體價值的終極詰問
“愛是火種,它能把靈魂燒成灰燼!”這是小說封面的一行話,既能作為全書的注腳,也可能概括人物糾纏的終極命題:在戰火頻仍、動盪不安的時代,個人對愛情、道德、信仰的渴望,究竟何以安放?誠如“冬季花園”這一意象,表面看只是凋零與冷漠,卻或許暗示著某種生之盼望與愛的脈動仍頑強地潛藏於凍土之下。只是每一個人能否真切感受到這份希冀,抑或會否在恍惚中走向毀滅?
全書多次在極度慘烈的殺戮場面後轉筆觸及人物間的隱秘溫情:在俄軍戰俘營裏,嚴一龍因救下高橋正夫而結下友誼;在大連紫金閣裏,許文娟始終念著舊情,不惜以身犯險……這種愛與死的交織場景,在揭示亂世人物精神狀態之餘,也對讀者提出詰問:人能否在深淵之中仍保持對真善美的希冀?如果能,又可否衝破時代?《冬季的花園》給我們的答案並不樂觀。儘管作品臨近尾聲時出現嚴一龍和高虎娃之間似有互助之跡,然而命運最終仍以猝不及防的暴力做出了回答。於是,關於救贖的思考尚未結束,卻早已演化為無可擺脫的悲涼。
一曲壯闊悲歌,荒雪中盛開的追問
《冬季的花園》是吳民民繼《海狼》等作品之後,時隔多年再次在大歷史框架下推出的長篇力作,也是他在“日俄戰爭到九一八事變”這個相對罕見關注的時段裏,對人物性格、民族糾葛、社會陰影做出的系統性書寫。作品既具有宏大的國際視野,又不失對個體命運的深情凝望;既融合了懸疑推理、群像刻畫,又通過冰天雪地的意象將悲劇美學發揮到極致。正如一些評論家指出的,這部小說可稱為歷史派懸疑的精心之作:它利用懸疑敘事帶來的閱讀快感,又遠遠超越了普通的破案主題,而成為對民族與國運、對戰爭與時代、對靈魂與愛的深切追問。
在技法上,作者通過多線交錯、遠景與特寫兼顧的方式,將眾多人物與事件有機融為一爐;在文字層面,既有白描式的殘酷場景,也不乏散文化的抒情筆觸;在主題層面,更用濃厚的悲劇意識來深挖人性底色,裹挾著人們對於清末民初東北地區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悲憫歷程的反思。小說結尾所謂“冬季的花園”並不是某種宏大變革或浪漫式的救贖,而是一種封閉、一種終極靜寂與無常。然而,也正是在這種沉重的無言之中,作者隱約為讀者保留了一線對人性微光的眺望。
有學者曾感慨,偉大的歷史小說不止於描繪往昔事件,更著力於打撈那些被大時代淹沒的卑微生命,同時也要為當下讀者提供反照現實的鏡鑒。從這個意義上,吳民民在《冬季的花園》中著力呈現的,不止是那段戰火紛飛的東北秘史,而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原下呻吟的亡靈之歌。它生動昭示出在無法逃遁的亂世中,人的苦難、情感與掙扎如何交錯出一片刻骨銘心的悲涼。也許,只有“冬季的花園”能容納那破碎得無法拾起的靈魂,而又讓我們讀者在其悲涼的意境中,體悟到歷史的警示與人性的反省。
《冬季的花園》的出現,無疑為當代文學增添了一種融國際視野、歷史深度與懸疑審美於一體的獨特創作實踐。它不僅延續了作家吳民民一貫的悲劇色彩與歷史意識,也再次佐證了以“逃”與“追”為書寫核心的敘事策略,如何引領讀者在跨越國界的亂局中,對正義與邪惡、愛與死、生與滅等命題發出新一輪拷問。其恢宏的格局與深沉的情感,使之成為一曲在“冬季”奏起、久久回蕩的文學悲歌,值得讀者與評論界長期回味與評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