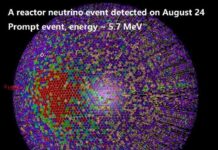中新社比利時那慕爾4月7日電 題:中國那麼遠,這麼近
——專訪比利時建築師戈建
中新社記者 德永健
在比利時南部那慕爾省一座僻靜的村莊,建築師戈建(Nicolas Godelet)坐在自己的工作室,專心致志地繪圖。就在這座村莊,他度過童年,至今仍與家人和父母住在這裡。
在家鄉工作和生活,戈建似乎沒有走遠,但工作室門口擺放的媒體文章又暗示,他已然走得很遠——這些對戈建進行專訪或報道的文章無一例外,都與中國有關。
深諳中國建築文化,講一口流利中文,參與設計北京冬奧會首鋼滑雪大跳台、山西平遙古城城市規劃、北京世界園藝博覽會比利時館、比利時駐華大使館新館……在比利時建築界,戈建是位不折不扣的“中國通”。2024年,關閉10餘年的布魯塞爾中國樓的修繕工作啟動,戈建再次參與其中。
近日,中新社“東西問”記者赴那慕爾專訪戈建,探尋他的中國之旅和中國故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常說自己是山裡長大的孩子,森林裡走出來的建築師,能否談談個人經歷?
戈建:我就在工作室外面的院落長大,周圍的環境都是田地、森林、山谷和河流。小時候一度覺得自己不走運,因為與城裡的孩子比,沒有時髦的衣服穿,不常去電影院,文化生活沒那麼豐富。
但回過頭來看,大自然送給我很多禮物。比如在森林裡玩的時候,我和小夥伴一起動手,蓋了一個“樹屋”,還看到很多用本地石頭建造的房屋、棧橋等,這些讓我對建築產生興趣。
15歲時,我帶著背包,開始獨自旅行,可以說這是我人生最大的變化,因為突然覺得國界可以跨越,人和人之間其實沒什麼區別。17歲時,我去了印度,在喜馬拉雅山遊覽,一年後我回到比利時,考入新魯汶大學,攻讀建築學。
中新社記者:您為什麼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
戈建:我在印度喜馬拉雅山邊境地區眺望過中國,但可以說不瞭解中國,因為當時歐洲關於中國的新聞報道很少,日常生活接觸到的中國人也很有限。
1996年我第一次到中國,是因為在一本雜誌看到新疆喀什的風景照片,覺得喀什非常遙遠,文化遺產豐富,很想看看這座絲綢之路上的古城,於是買了機票先飛到北京,然後一路輾轉到喀什。
這段旅程改變了我對中國的印象。原來,我以為中國人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中國人很嚴肅,中國與其他亞洲國家差不多,結果發現並非如此。中國與眾不同,寬廣的草原和遼闊的土地讓我覺得中國很美。
回到比利時後,我在大學選修漢語和東方文字課程,重點研究甲骨文和腓尼基字母,希望發現象形文字書寫形式與建築藝術之間的聯系。2002年我再次來到北京,先是留學,後來成立了建築工作室。
中新社記者:您參與設計北京冬奧會首鋼滑雪大跳台、山西平遙古城城市規劃、比利時駐華大使館新館等一系列引人矚目的建築項目,對於東西方建築文化的交流與合作,有何心得與體會?
戈建:與比利時相比,中國設計大型建築項目的機會更多,比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2022年北京冬奧會,可以滿足一名建築師的雄心壯志,尤其是對年輕建築師而言。
我十分喜愛中華文化,認為建築項目一定要尊重當地文化,不能照搬國外設計,把建築變成“遊樂園”,這可能是我參與山西平遙古城城市規劃的原因之一。參與設計北京冬奧會首鋼滑雪大跳台時,我借鑒了德國老工業區的改造經驗,強調不能“大拆大建”,應樹立分拆改造、與自然共生、循環利用等理念,而且要兼顧環境保護和經濟效益。
在北京工作期間,有時我還是一座“橋樑”。比如中國國家大劇院建設期間,我曾擔任保羅·安德魯(主持設計中國國家大劇院的法國建築師)的翻譯。其他人不懂柱子、焊接一類的建築術語,讓他非常著急,我和他都說法語,都是建築師,溝通交流更加順暢。
中新社記者:您研究甲骨文與建築藝術之間的聯系,當年把北京的工作室放在一座四合院。對於中國建築文化,您有何理解?
戈建:中國建築文化有“風水”一說,告訴你不能隨便蓋房子,要先分析環境,研究怎麼向陽,怎麼防風,怎麼流水,空間設計要注意舒適度、私密性、安全感等,從建築師的角度看,“風水”蘊含一定的科學理念,體現“天人合一”哲理。
還有中國古建築常見的榫卯結構。歐洲建築常見三角形結構,是不可變形的,但在榫卯結構中,榫與卯之間有間隙,是可變形的,一旦發生地震,建築能够通過這些變形吸收地震造成的衝擊,有利於建築抗震。榫卯工藝在中國代代相傳,可以說是獨一無二。
中新社記者:對於推動比利時與中國建築文化交流與合作,您有何建議?
戈建:當下,比利時建築文化強調綠色節能、循環利用、可持續性等。比如我參與設計比利時駐華大使館新館,使用了木結構技術,也許很多人認為“過時”,但木結構建築實際上非常低碳環保。我們還將舊館拆下的磚塊打碎,重新製成新磚,砌在新館的牆壁,體現了循環利用理念。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建築傳統和建築風格,但我們可以尋找精神層面的“共同點”,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低碳節能”等,通過科學設計和深入研究合理利用資源,實現人、自然、建築三者的互動共生。(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