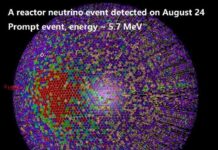中新社北京5月28日電 題:博物館在快速變化的社會中正經歷何種角色變革?
——專訪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研究員沈辰
作者 劉洋
在科技浪潮的席捲下,社會公眾的文化需求正日益多元化,全球的博物館也正在經歷角色的變革。博物館行業面臨怎樣的挑戰和機遇,其社會功能正在怎樣變化?策展人應當如何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文物?近日,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以下簡稱“ROM”)研究員沈辰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採訪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博物館行業當前面臨的挑戰和機遇是什麼?博物館的社會功能角色正經歷怎樣的變革?
沈辰:當今社會發展迅速,數字技術的普及重塑了公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的文化消費習慣,他們追求更便捷、個性化的體驗。
公眾對文化體驗的定義已經擴大,包括了更廣泛的一系列活動,如公共藝術、美食和街頭集市。觀眾對博物館期待值以及文化消費觀的變化也影響著博物館的轉型。博物館、圖書館等文化場所的功能已突破傳統邊界。博物館和公眾的關係不再祗停留於“公共教育”的層面。觀眾的文化需求正發生改變,審美疲勞、代際差異等都影響著博物館的策展選題。將公眾體驗視為博物館未來發展的中心環節,為了公眾而收藏、研究、展示,博物館從業者需要探索新一代各族青年的興趣點。
東西方博物館雖然發展歷程與速度不同,但在社會功能角色變革和轉型方面具有相似之處。以西方博物館為例,自20世紀中期開始,隨著藏品的全球化,博物館希望利用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藏品發揮“警示育人”的教育目的。博物館嘗試去解釋曾經一度與歐美國家“相隔絕的”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文化。這一時期的博物館展廳經翻新後可被視作一本“橱窗式”的文物教科書,向觀眾展示中學教學大綱中往往被忽略的那一部分“世界歷史”。
到了21世紀,隨著博物館觀眾群體的全球化趨勢以及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博物館此前為了實現教育職能而全是藏品的方法過時了。人們隨時可以在網上搜索相關文物歷史。博物館正逐漸轉型為能够讓公眾可以結合時事去尋找權威的話語權和討論焦點、熱點的論壇,通過更加接地氣的知識對話為觀眾帶來學習的愉悅,為社會打造一個益民親民的文化中心,讓反傳統、非主流的展覽也有一片天地,啟發觀眾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社會的關愛。
中新社記者:西方博物館在策劃中國主題展覽時如何選擇代表性文物?您如何定義“代表性”?
沈辰:海內外博物館常舉辦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的展示和表演,例如ROM的年度文化遺產日,其中包括了中國文化遺產日。在這一天,博物館與當地的民族文化機構和團隊合作舉辦民族表演活動,如擊鼓、舞獅、舞龍等。觀眾往往認為這些活動是典型的民族文化。但在單一地區流行的非物質文化表現形式,並不能真正代表中國多元文化民族的全部文化遺產認同。
比如中國彝族的賽裝和插花,經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專業博士何鑒菲的多年考察和走訪發現,我們如今所熟悉的彝族文化中的典型代表賽裝和插花是近幾代人不斷延續改造後編排出來的結果。這種文化遺產代表不是用對和不對來區分,而是需要我們通過研究並抱著開放的思維去思考。博物館需要平衡何鑒菲的學術研究和大姚縣彝族自我文化認同之間的差異進行策展與釋展。通過博物館的展覽和表演,引導觀眾對文化遺產認同這一系列問題的關注和討論,是博物館需要在展覽背後認真思考的問題。在策劃相關展覽時,我們可以邀請當地的學者和百姓發表看法,使得展覽更具包容性。
此外,以往東西方博物館都試圖展出中國的珍寶級文物,以“倉儲式的珍寶櫃”的展櫃設計呈現文物,強調稀有性和視覺衝擊力,激發公眾對異域文化的想象。但隨著社會的加速變化,此種展示方式已不再具有同等吸引力。
策展人需要考慮不同代際、不同民族和地區的民眾感興趣的議題,將其與中國的文物結合起來,讓西方的觀眾瞭解中國不同時期是否有相似的社會議題。人們在觀展中逐漸意識到相距甚遠的種種文化差異居然可以從歷史文物中找到許多共性,世界並非割裂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全球文化遺產”與“歷史正義”兩者間的關係?
沈辰:18世紀到20世紀初,技術革新和全球貿易發展引發大規模全球藝術品收藏。這種藝術品收藏的風潮是“西方列強”國家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單向”全球化,是西方國家殖民化過程中的一種結果。在中國,這種殖民化下的西方博物館藝術收藏史是以“火燒圓明園”為標誌的。
無論一個博物館的文物收藏史是否有它的獨特性和合法性,殖民時代西方國家的掠奪性收藏永遠是時代留下的切膚之痛。這種文化收藏不僅是19世紀西方工業強國,以所謂“遺產保護”之名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進行的物質文化掠奪,也是對當地土著文化遺產的佔有。
從21世紀初開始,以美國文學界和學術界為先鋒,對博物館的藏品歸屬發起了一場又一場辯論。由於美國一系列保護原住民文化遺產的法律相繼出台和執行,博物館因早年考古出土而收藏的原住民祖先遺骸和宗教文物都被要求退還。後來,原住民文物退還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一模式開始運用到其他追索案例上。1997年,我被邀請參加ROM的一個由文物歸還政策制定委員會組織的會議。20多年後,ROM按照這個政策開始對安大略省原住民的文物和遺物進行退還。
所以無論是否按照西方法律來判斷博物館藏品的合法擁有權,殖民化下的全球藝術和文物在倫理道德上還是有歸屬性的。每一件在海外博物館收藏的流失文物背後都有一段國仇家恨的悲涼故事。但如果簡單粗暴地把這筆賬算到博物館頭上也是難以讓人信服的。比如博物館具有齊備的合法收購、收藏手續,但賣方來源的合法性難以核實,尤其是在1970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出台之前的文物交易。
西方博物館如何處理這些流失文物?是否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如何向公眾闡釋這些文物背後的歷史?這些問題直接反映了其對殖民歷史的態度。而當觀眾能够從展覽中思考為何一件中國的文物會被收藏在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博物館裡時,這件“異鄉的國寶”也就實現了在本土語境下難以實現的意義和價值。(完)
來源中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