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學大德”的審美倫理學
——呂國英“氣墨靈象”藝術論核心命題深度闡釋
艾 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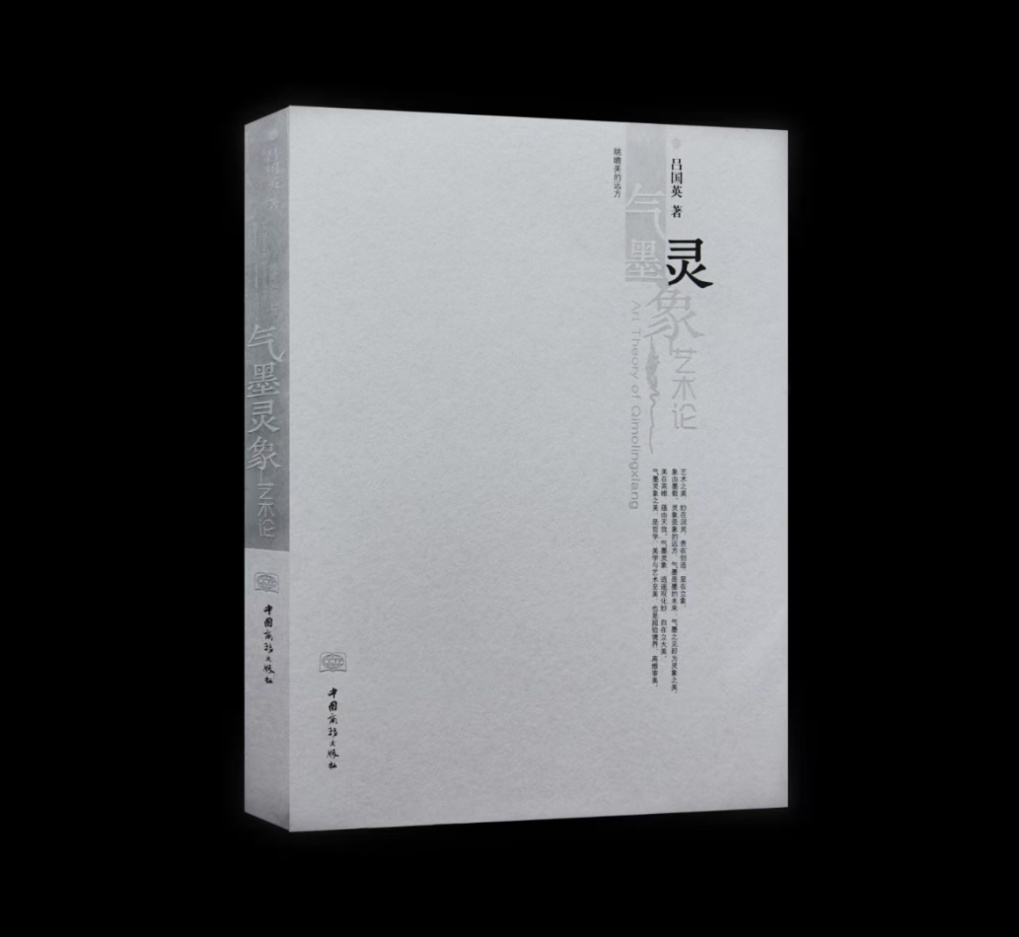
在當代藝術理論面臨價值失序與批評失語的語境下,呂國英先生構建的“氣墨靈象”藝術論以其恢弘的理論體系和前瞻的美學視野,為藝術本質的思考提供了全新範式。作為該體系的第五大核心命題——“高學大德”方入至美審美,不僅承載著對藝術家主體修為的深刻要求,更蘊含著對藝術本體的倫理學轉向思考。本文將從理論定位、內涵解析、歷史互證、現實意義及學術反思五個維度,對這一命題展開深度解讀。
一 理論定位:藝術終極境界的主體性基石
在“氣墨靈象”藝術論的宏大架構中,“高學大德”論被明確定位為“補論篇”——既是對前四篇立論的補充,又是對理論體系的圓滿與延伸。這一特殊定位揭示了其在理論系統中的樞紐作用:前四篇分別聚焦“靈像是象的遠方”(逸形入靈 大藝立象)、“氣墨是墨的未來”(如氣化墨 載靈承象)、“氣墨靈象互為形式內容”(氣墨繪畫 靈象藝術)、“藝法靈象揭示藝術本質規律”(藝法靈象 至美審美),而本篇則直指藝術創作的主體根源,即“誰才能抵達氣墨靈象之境”這一核心問題。
從理論邏輯看,呂國英構建了嚴密的概念遞進鏈:“靈象”作為藝術形式的終極形態(象的遠方)需要“氣墨”作為載體(墨的未來);“氣墨靈象”的完美統一構成藝術本體的至高境界;而“高學大德”則是實現這一境界的主體條件。四者形成“形式—載體—本體—主體”的閉環邏輯,正如其所強調:“惟高學大德者,方達氣墨靈象之境,而至氣墨靈象者,非高學大德而非所能為。”在此意義上,“高學大德”論填補了“氣墨靈象”從理論可能走向創作現實的關鍵一環。
更深層的理論價值在於,呂國英將藝術家修養提升至藝術本體論的高度進行探討。傳統藝術理論中,藝術家素養多被視為創作前提或輔助條件,而在“氣墨靈象”體系內,“高學大德”與“氣墨靈象”被賦予同構性關係——兩者“亦屬並列關係,或稱同位之語,兩者同行相攜、缺一不可,皆至最高處方可實現各自之‘自我’。”這種理論建構徹底打破了創作主體與藝術本體的二元分立,建立起審美倫理學的闡釋框架。
二 “高學大德”的雙重維度與精神內核
“高學大德”作為複合概念,包含知識論與倫理學兩個向度,其內涵遠超傳統“藝德”範疇,呈現出獨特的理論深度。
1. “高學”:超越技藝的知識譜系
“高學”在呂國英的理論體系中絕非簡單的知識積累,而是指向多層次的知識構成與跨學科的視野融合——
藝術史的通透把握:藝術家需“讀藝論史”,通曉“六朝三傑”“隋唐五代十大家”“兩宋十二傑”“元明八大家”等藝術流變,理解藝術史的選擇邏輯與價值標準。這種歷史意識使創作避免成為無源之水。
藝術規律的深刻認知:掌握“藝法靈象”這一“揭示藝術本質規律”的終極法則,理解藝術演進中“尚絕”(原創性)、“尚新”(創新性)、“尚進”(超越性)的內在驅動力。
跨學科的知識視野:從呂國英對“大火箭”“射電望遠鏡”“量子衛星”等科技載體的援引可見,“高學”包含對科學、哲學等多元領域的融會貫通,體現天人合一的宇宙觀。這種開闊視野使藝術創作能承載更恢弘的精神維度。
值得注意的是,“高學”的終極目標是培養藝術家的形式創造力。呂國英尖銳指出當下藝術亂象源於“陳、俗、髒、假、亂、死”的筆墨困境,而突破此困境需通過學識涵養孕育“氣墨”這一“墨的未來”——即超越線墨、意墨、潑墨、樸墨的終極筆墨形態。
2. “大德”:藝術家的倫理高度與精神境界
“大德”論直指藝術家的精神品格與價值擔當,其內涵包含三個不斷昇華的層次——
專業倫理層:抗拒“浮躁與急功近利”“投機取巧,沽名釣譽”等職業異化,保持藝術創作的純粹性。這要求藝術家抵制市場誘惑,避免陷入“以‘職’定價,以‘銜’論價”的價值錯位。
文化擔當層:樹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批判“以洋為美、以洋為尊、唯洋是從”的殖民心態。呂國英特別強調藝術家需克服“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的歷史虛無主義,這與其對中華美學精神的堅守一脈相承。
宇宙生命層:最高層次的“大德”體現為“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宇宙情懷與“實現自我救贖”的生命超越。在此境界,藝術創作成為參悟天地大道的修行方式,藝術家通過“極限挑戰、生命自由與自我救贖之犧牲”,抵達“潤靈樂境”的超驗審美。
表:傳統藝術家修養觀與“高學大德”論比較
維度 傳統修養觀 “高學大德”論 理論突破點
目標指向 技藝提升 靈象境界達成 從技術到本體的跨越
知識結構 師徒經驗傳承 跨學科通識體系 打破藝術封閉性
倫理範疇 個人品德 文化擔當與宇宙情懷 倫理維度擴展
歷史觀照 摹古為尚 尚絕尚新尚進 動態發展史觀
三 藝術史觀的互證邏輯
呂國英對“高學大德”的論證,並未停留於理論推演,而是構建了與藝術史選擇機制的深刻互證。他通過對中西藝術史的重新解讀,揭示了藝術史本身就是一部“高學大德”者的篩選史。
1. 藝術史的“五尚”選擇標準
呂國英提煉出藝術史擇錄經典的五大核心標準,構成嚴密的史學價值體系——
“尚絕”的原創律:“尚絕居於‘五尚’之首”,其核心是原創性、唯一性、不可重複性。呂國英以人類文明史類比:世界公認“四大古代文明”(中華、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皆因原創性入選,而古希臘文明因融合古巴比倫與古埃及文明,古波斯文明因融合古巴比倫與古印度文明,皆因缺乏唯一性價值而被排除在“原創文明”之外。藝術史同樣如此,“選擇了郭熙,就不可能再選擇張熙;載錄了李成,就決可能再載錄王成;高迎了畢加索,就不可能再高迎牛加索。”這種排他性原則決定了藝術史對模仿、複製的徹底否定。
“尚新”的進化律:“新”是“舊的揚棄與超越”,但絕非割裂傳統的標新立異。呂國英強調真正的創新是“繼承之創新,也是站在歷史高點的前行,立於巨人肩膀的攀登”。他以張僧繇的“沒骨”技法(繼承凹凸畫法)、李成的“自成一家”(師承荊浩、關仝)、黃賓虹的“黑賓虹”(自我圖新)、齊白石的“紅花墨葉”(師法八大山人等)為例,說明偉大創新皆具歷史承續性。同時他尖銳指出:“沒有繼承的創新無意義;沒有創新的繼承同樣無價值”,對泥古不化與虛無主義進行雙向批判。
“尚進”的超越律:從“進”的造字本義(“進”,取“追鳥”而“向上攀登”之義)出發,呂國英強調藝術史是一部“向上,就是前行,就是發展與演進、攀登與超越”的歷史。這種超越既體現為個人風格的不斷精進(如黃賓虹從“白賓虹”到“黑賓虹”的蛻變),也體現為藝術形式的代際躍升(如西方藝術從印象派到現代主義的流變)。
“尚融”的會通律:雖在本文未充分展開,但從呂國英整體理論可見,“氣墨靈象”本身即是中西美學融合的產物——既承中國古典美學“氣韻”“意象”傳統,又融西方現代藝術抽象表現與超驗精神。
“尚極”的終極律:藝術史選擇始終指向極致性探索,這正是“氣墨靈象”作為“筆墨未來”與“象之遠方”的歷史依據。
表:藝術史“五尚”標準例證
標準 內涵 中西藝術史例證
尚絕 原創性、唯一性 郭熙《早春圖》、畢加索《亞維農少女》
尚新 繼承中創新 齊白石“紅花墨葉”、塞尚後印象派
尚進 向上超越 黃賓虹“白”變“黑”、馬蒂斯野獸派
尚融 跨界融合 林風眠中西合璧、趙無極抽象山水
尚極 終極探索 八大山人簡約極致、羅斯科色域繪畫
2. 主體修為與藝術史定位的因果律
呂國英通過藝術史反證:“高學大德”是藝術家進入藝術史的必要條件。他特別指出藝術史對“近親繁殖”的天然排斥:“藝術史上,鮮有子承父業而成大家者…藝術史從來拒絕‘近親繁殖’,不僅如此,或往往為‘手足’相‘殘’、斷‘子’絕‘孫’之‘見證’。”這一現象深刻說明:藝術史選擇的是具有獨立精神與開創性貢獻的個體,而非技術傳承的家族譜系。
更深層的歷史啟示在於:偉大藝術家的養成需要學識與德性的共生。呂國英以歷代大家為例——從張僧繇對凹凸畫的吸收轉化,到李成在荊浩、關仝基礎上的創新,再到黃賓虹、齊白石的衰年變法——無不體現“高學”的支撐;而他們抗拒流俗、堅守藝術理想的生命姿態,則彰顯“大德”的境界。正是這種雙重修為,使他們能夠回應藝術史“尚絕、尚新、尚進”的召喚,成為藝術史的座標點。
四 當代藝術困境的破局啟示
呂國英提出“高學大德”論,絕非空泛的道德說教,而是針對當下藝術生態深重危機的銳利診斷與救治藥方。他對藝術亂象的剖析直指病灶:
1. 亂象根源:主體修為的集體塌方
在《藝法靈象 至美審美》一文中,呂國英曾系統列舉藝術領域的八大亂象,這些亂象在“高學大德”視角下均可歸結為藝術家主體修為的缺失:
“高學”缺失的表徵:創作中的“抄襲模仿、千篇一律”源於藝術史認知的貧乏;“複製性生產”暴露創新能力的衰竭;“追求形式、缺少內容”反映思想深度的空洞;“蔑視傳統、遠離現實”體現文化根脈的斷裂。
“大德”塌陷的症候:市場中的“以‘職’定價,以‘銜’論價”暴露價值觀念的扭曲;“浮躁與急功近利”顯現職業倫理的失守;“江湖氣、‘圈子’化”折射獨立精神的淪喪;“庸俗吹捧、阿諛奉承”標誌批評風骨的消解。
尤為深刻的是,呂國英將“以洋為美、以洋為尊”的文化自卑心理,歸因於藝術家“缺少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德性缺失。這種診斷超越了簡單的現象批判,深入到文化主體性重建的倫理高度。
2. 破局之道:重建創作倫理的雙重進路
基於“高學大德”論,呂國英為當代藝術困境開出極具實踐智慧的藥方:
“高學”養成體系——
藝術史重估:重讀經典,理解“藝術史就是藝術巨制的歷史,也是關於藝術大家的歷史,還是關於藝術形式語言、流派演變、發展的歷史”,避免陷入“中國畫窮途末路”等歷史虛無主義陷阱。
跨學科通識建構:突破藝術學科壁壘,融入科技、哲學、人文等多維知識,培養如“量子衛星”般承載“靈象”的創新性思維。
筆墨傳統再生:通過“氣墨”理論(從線墨→意墨→潑墨→樸墨→氣墨的演進),為筆墨困境提供解決路徑,使形式語言重獲生命力。
“大德”培育機制——
創作心態淨化:抵制“心緒浮華、精神迷離”的浮躁症候,回歸“殫精竭慮,苦心造詣,一境恒求”的創作本真。
文化主體性重建:摒棄“去中國化”“去主流化”的自我殖民,在“中華美學精神”傳承中確立文化自信。
超驗境界追求:超越功利境界,向“潤靈樂境”“超驗境界”的精神高度昇華,使藝術成為安頓生命的修行方式。
這一理論對當下文藝高峰建設具有直接指導意義。呂國英強調:“新時代需要文藝大師,也完全能夠造就文藝大師!新時代需要文藝高峰,也完全能夠鑄就文藝高峰!”而造就大師與鑄就高峰的關鍵,正在於藝術家群體“高學大德”修為的集體性提升。
五 學術反思:理論貢獻與開放性問題
作為極具原創性的理論建構,“高學大德”論在貢獻重要思想資源的同時,也留下若干值得深入探討的學術空間。
1. 三大理論貢獻
重構藝術家修養與藝術本體的關係:突破傳統“畫品即人品”的道德化簡單比附,建立起“高學大德”與“氣墨靈象”的本體論聯結。在此框架中,藝術家修養不再是外在要求,而是藝術本體實現的內在條件,兩者在“天人合一”的哲學高度獲得統一。
確立藝術史選擇的倫理維度:通過對“五尚”標準(尤其“尚絕”“尚新”“尚進”)的闡釋,揭示藝術史不僅是形式演變史,更是精神價值的篩選史。這種史觀為藝術評價提供了超越風格分析的倫理尺度。
提供藝術批評的元理論框架:面對藝術批評中“庸俗吹捧、阿諛奉承”等亂象,“高學大德”論確立的雙重標準(學識深度與精神高度),為批評實踐重建了價值座標。
2. 待深化的開放性問題
“高學”的知識邊界問題:在學科高度分化的當代,“高學”所需的知識廣度與深度是否存在合理邊界?如何避免陷入“博而不精”的知識困境?呂國英的理論需要進一步明確知識結構的優化模型。
“大德”的歷史具體性挑戰:不同歷史語境中“德”的內涵存在顯著差異(如八大山人的遺民氣節與徐悲鴻的愛國情懷),“大德”的普遍標準如何與歷史特殊性協調?這要求理論增加歷史辯證法的維度。
修為與天賦的張力關係:藝術史中不乏修為不足卻天賦卓絕的案例(如卡拉瓦喬),“高學大德”是否可能過度理性化藝術創作的神秘維度?理論需進一步解釋天賦與修為的辯證關係。
結語:藝術倫理學的當代重構
呂國英“高學大德”論的價值,遠超出個體藝術家修養訓導的範疇,實為藝術倫理學的當代重構。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價值激烈碰撞、藝術市場異化創作生態的今天,這一理論以中華美學精神為根基,融通中西藝術智慧,為藝術創作確立了學識與德性雙重超越的倫理座標。
其對“氣墨靈象”境界的追求,既是對中國古代“大音希聲,大象無形”(老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美學傳統的現代詮釋,也是對西方“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黑格爾)、“美在自由”(康德)等命題的創造性回應。而“高學大德”作為抵達這一境界的主體路徑,更凸顯了知行合一的中國智慧——藝術至境的實現,終究依賴於藝術家在學識攀登與德性修煉中的生命證悟。
當下中國藝術正處在攀登高峰的歷史節點,“高學大德”論所彰顯的創作倫理重建,或將成為破解藝術亂象、鑄就時代經典的關鍵密鑰。如呂國英所期許:“沐浴‘雙代’盛會春風”,這一理論將助力文藝工作者“認知文藝演進諸象、建構藝術創作新理念、新思想,進而實踐藝術創新”,在中華文化復興的宏大敘事中書寫藝術的華彩篇章。
(論文原文載:《解放軍報》長征副刊、《文藝報》《人民政協報》學術家園、《“氣墨靈象”藝術論》·中國商務出版社;《粵海風》《中華時報》理論連載等)
2025.05.12·北京
附
呂國英 簡介
呂國英,文藝理論、藝術批評家,文化學者、詩人、狂草書法家,原解放軍報社文化部主任、中華時報藝術總監,央澤華安智庫高級研究員,創立“氣墨靈象”美學新理論,建構“哲慧”新詩派,提出“書象·靈草”新命題,抽象精粹牛文化。出版專著多部、原創學術論文多篇,撰寫哲慧詩章兩千餘首。
主要著作:《“氣墨靈象”藝術論》《大藝立三極》《未來藝術之路》《呂國英哲慧詩章》《CHINA奇人》《陶藝狂人》《神雕》《國學千載“牛”縱橫》《中國牛文化千字文》《新聞“內幕”》《藝術,從“完美”到“自由”》。
主要立論:“靈象”是“象”的遠方;“氣墨”是“墨”的未來;“氣墨”“靈象”形質一體、互為形式內容;“藝法靈象”揭示藝術終極規律;美是“氣墨靈象”;“氣墨靈象”超驗之美;“書象”由“象”;書美“通象”;“靈草”是狂草的遠方;詩貴哲慧潤靈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