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構成佛教龐大的教法體系中,大乘菩薩信仰佔據重要地位,與思辨性很強的教理互相補充、相輔相成。菩薩信仰內容大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佛經記述的菩薩神聖事蹟和教法、信眾的崇信供奉及其儀軌、菩薩應化道場和聖靈顯化的傳說、菩薩信仰的名山勝境以及相關佛寺遺跡、駐錫高僧、朝野巡禮供奉情況等。
中國佛教以大乘佛教為主體,菩薩信仰深受廣大信眾的重視,在社會廣為流行。唐代道宣《釋迦方志》卷下介紹,兩晉南北朝時期除盛行阿彌陀佛信仰之外,最流行的是對觀世音菩薩、地藏菩薩、彌勒菩薩(或彌勒佛)的信仰,四方信眾崇奉供養並向這些菩薩祈禱求救的人很多。其中道宣未提到的文殊菩薩信仰,實際在進入南北朝以後已逐漸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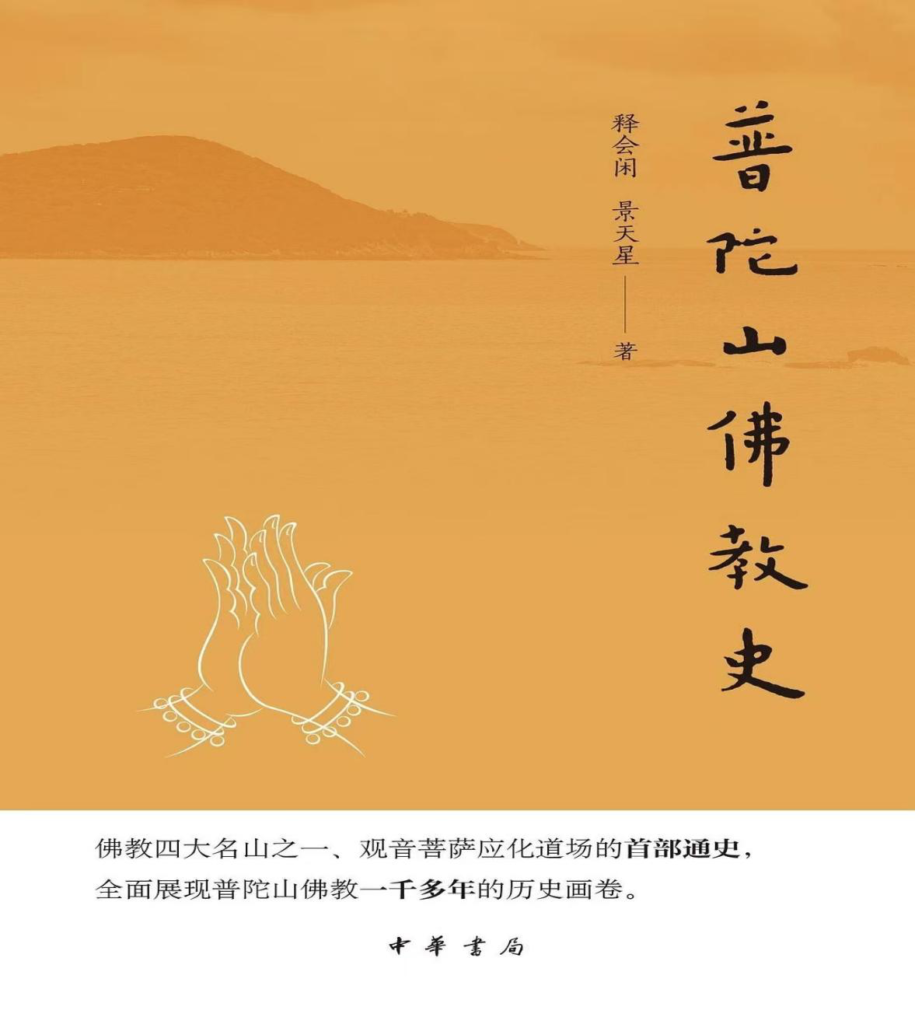
菩薩,乃梵語音譯“菩提薩埵”之略,意為修持“六度”,“以智,上求菩提;用悲,下教眾生”,矢志踐行“菩薩之道”的大乘佛教修行者。所謂“菩薩之道”,大體可概括為“悲、智、行、願”四個方面。
隋唐以後直至明清,中國佛教逐漸興起並崇奉的“四大名山”或“四大菩薩道場”——浙江普陀山、山西五臺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華山,分別被奉為“大悲”觀世音菩薩、“大智”文殊菩薩、“大行”普賢菩薩、“大願”地藏菩薩的應化道場。這也是考察和研究中國佛教史不可忽視或缺的重要方面。
迄今對以上被奉為菩薩信仰中心四大名山的研究雖仍嫌不足,然而已經取得可觀的成績。比較而言,對四大名山中的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的研究成果較多一些,並且早有通史之作,此後在對安徽九華山地藏菩薩道場的研究中也有了通史著作,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在對峨眉山普賢菩薩道場和普陀山觀音道場的研究中尚沒有連貫記述的通史性著述面世。
可喜的是,繼2024年7月中華書局出版了釋會閑、景天星二人合著的《普陀山佛教史》之後,9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永壽法師著的《峨眉山佛教史》,終於添補了四大名山菩薩道場研究中的兩項空白,應當說這是中國佛教界和學術界可喜可賀的大事。
這裏僅就釋會閑、景天星合著的《普陀山佛教史》的面世說上幾句,並表示衷心的祝賀。
普陀山地處東海之上,自五代後樑始建“不肯去院”,自從宋朝皇帝降勅改建和賜額“寶陀觀音寺”,並置田積糧、許歲度僧、供奉香火之後,才逐漸香火興旺起來,歷經元、明、清而發展為遠近聞名的觀音菩薩信仰道場。
回顧歷史,自元末以後,長期劫掠肆虐中國北部沿海的倭寇開始轉至東南,從此江浙閩粵沿海一帶不再安寧。迫於形勢,明太祖洪武年間勅信國公湯和強徙東南沿海之民遷往內地,致使普陀山殿宇遭到焚毀,觀音造像被遷至寧波的棲心寺(今七塔寺),普陀寺一度與棲心寺合併。在明成祖永樂十七年(1419)明軍於遼東全殲來侵倭寇,海防轉為平靜。普陀寺在明憲宗成化(1465—1487)年間曾得以恢復。然而進入明世宗嘉靖時期,倭寇之患複轉猖獗,普陀寺又被迫內遷,舟山甚至被倭寇強佔作為對抗明軍的據點。在明軍全殲倭寇之後,普陀山又得以興複。然而不久進入清初,清廷為平定南明殘部和反清義軍等,嚴格實行“海禁”,寺院又一次遭到殘毀,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復臺灣之後,海禁漸次弛緩,普陀山僧眾才陸續返回故土重建寺院,逐漸恢復活動。正如民國時期王亨彥撰《普陀洛迦新志》所概括的那樣:
明洪武二十年(按:1387年),起遣定海,寺殘僧散,蕩為荒煙蔓草者百餘年。成化時,漸漸興複。嘉靖三十二年(按:1553年),又複內徙。隆慶六年(按:1572年),又事興複。至萬曆中為極盛。自萬曆至清初,才數十年,海氛不靖,屢遭寇擾。至康熙十年(按:1671年),定海縣廢,僧複內徙,寺院殘毀,存者十無一二。二十三年(按:1684年),海禁大弛,僧歸故土。
舟山普陀山歷經以上曲折變遷和磨難的情景,正是明初至清朝收復臺灣以前江浙沿海嚴重動亂和最後趨於安定的歷史縮影。
可以想見,要厘清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考察和論述普陀山佛教的歷代盛衰、觀音道場的興廢,難度是很大的。好在作者最終克服重重困難,在搜集豐富翔實的資料,廣泛閱讀和吸收國內外有關研究資料之後,細心地加以梳理和思考,終於將《普陀山佛教史》撰寫完成。
縱觀全書,結構嚴謹合理,文筆也比較通暢,對普陀山地理環境、佛教傳入歷史、自宋元明清直至近代佛教傳播的情況,有關普陀山寺院殿堂的建築、歷代駐錫高僧及其傳法著述、普陀山志的編纂、觀音菩薩信仰在民間的流傳情景等,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考述。
最後,衷心祝願普陀山觀音道場、佛學院和廣大僧俗信眾,在這舉國上下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中華民族新時代文明而努力奮鬥的新時代、新征程中,作出新的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楊曾文

